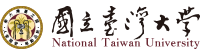狄更斯的中文及臺語聖誕頌歌
如果由我來寫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的小說,那麼恐怕有一半臺大的校友可以寫得比我更好。但是這幾天正好遇上了一個有趣的經驗,使我決定在聖誕節就要到了的時候,寫一篇有關他的《聖誕頌歌》(A Christmas Carol)的文章,同時迎接明年他210年的誕辰(二月七日)。
狄更斯的小說、散文和戲劇非常的多,是一個文學大家,這個不用我多說。一般華人最知道的當然是他的《雙城記》,但是在臺灣,可能知道他的《聖誕頌歌》的人更多,因為它經常被人搬上教會的舞臺,是聖誕節最常見的慶祝活動。它幾乎定義了所謂聖誕的意義和慶祝的精神,雖然大部分的人都以為聖誕節是一個歡樂的節期,是休息、放鬆、乃至於狂歡的日子。狄更斯卻通過這麼一個小說來告訴我們聖誕節是一個寬大為懷、濟助窮人和家人團聚的時候,人們要紀念生活的富足和意義,並且滿懷感激,相互恭喜聖誕所帶來的幸福、希望和快樂。
故事的本事簡單說就是有一個非常吝嗇的財主,名叫司孤寂(Scrooge)醒悟聖誕節日意義的故事。故事從聖誕夜的下午開始。天已昏暗,但是他還逼著他的夥計工作,毫無聖誕的歡樂之情,甚至還在夥計苦苦哀求之後,才勉強放他聖誕日一天的假,更叮囑他過完節就必須提早回去上班。那天晚上,吝嗇的司孤寂回到家,竟然在寒冷、家徒四壁的房間裏看到了他已經去世七年的夥伴,這位夥伴身上綁滿鐵鏈,一副疲乏不堪的樣子,警告他說在那天晚上他會遇到三個鬼。他們要帶給他重要的信息。
果然那天晚上司孤寂遇到了三個鬼,各是司孤寂的前身,現在和未來的鬼靈。第一個鬼帶他去看他過去如何輕視聖誕節,吝嗇小氣,以至於不能與他們分享聖誕的喜樂。司孤寂看到了自己貪婪孤獨的作為,驚嚇不已。
第二個鬼代表的是當前的司孤寂。這鬼帶了司孤寂去看他夥計在家裏團圓聚餐。雖然他們貧窮,桌上的事物也很簡單,但是他們卻顯得十分的高興,享受著聖誕的幸福和快樂的氣氛。司孤寂不能不警覺到他們的快樂乃是對他最大的諷刺。當司孤寂和鬼靈遇到兩個生來無知又貪婪的小孩子時,司孤寂忽然發起同情的感慨,那鬼就模仿司孤寂自己的聲調和口氣來嘲笑他說:「難道沒有監獄嗎?難道沒有救濟院嗎?」一向缺乏憐憫心的司孤寂深自慚愧到無地自容。
第三個是未來之鬼,他帶著司孤寂去看在聖誕日孤零零去世的司孤寂自己。他的墓沒有人打理,更還有人為他的死感到高興。
結局是司孤寂悔悟以往的生活方式,立志要徹底改變自己:從此以後,他要熱心助人,實踐聖誕感恩與助人的真諦。
這個小說所描繪的聖誕精神影響了全世界,代表維多利亞女皇時代的基督教生活的態度(雖然現在新的、由彼得蓋伊(Peter Gay)提出的解釋已經對當時的生活理想和實際做出嚴肅的挑戰): 平實而和諧的生活哲學;聖誕節乃是一個必須心境愉快,迎接家人的團圓,不忘窮困人的需要,是樂善好施的日子。
《聖誕頌歌》因為把鬼寫進了小說裏,所以從非常嚴肅的基督教立場來看,它似乎不是很正確的宗教小說,所以有的基督徒並不是很認同它(就像現在還是有基督教徒反對《哈利波特》小說一樣)。不過這本書和它的影響不能否認是非常的巨大,把基督教的關心從個人的拯救帶到一個社會公義的層面,並對19世紀英國多數自由主義份子所主張的社會改革做出批判性的認同,認為社會改革還必須符合基督教的公義。
大部分19世紀英國的自由主義信徒對於傳統基督教的信仰的確採取著一種相當開放的態度,否定《聖經》和基督教傳統裏面許多不合科學的記載。雖然基本上他們接受基督教的道德教訓,但是不受傳統教義的束縛。狄更斯大致上也是如此,但是他死後七十年左右,一本他自己寫的「基督傳」(The Life of Our Lord)出現了。這本書是他寫給自己的家人的,並不擬出版。不過到了他最後的兒子都已經過世了之後的1933年,孫輩兒女們多數人同意決定將它出版,於是這本書開始流行於世。「基督傳」證實了狄更斯個人的基督教信仰,但是在世的時候,他卻不公開自己這個基督教的信仰。他大部分的時候表現出自由主義份子對社會不平等及貧窮痛苦的關心,但是他還是主張社會制度的改進或改良並不夠,更需要懷抱同情心,這樣才是個人生活的理想高度。他對於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演化學說並沒有反對之意,甚至還曾在文字間表示認同。對於當時的人來說,他不排斥達爾文的演化論是完全可以瞭解的。
大部分研究狄更斯的學者不太愛提起這本書,理由很簡單。而書中偶有污衊猶太人的字句也當然是現代文學潮流所不能接受的態度。
很有趣的,這本書在出版的時候卻在中國至少有三個雜誌刊登了出版的消息。我個人的猜想是因為自從林紓介紹了狄更斯以後(1907-1908兩年中計翻出五部),中國人很喜歡他帶有同情心的人道主義小說,所以會促成那麼快速的翻譯。事實上,在70年前的1942年,成都新蜀圖書文具公司出版的《金沙文藝》雜誌竟然出版了紀念狄更斯130年誕辰的特刊。足見他在中國受歡迎的程度。
《聖誕頌歌》在1913年後被翻譯成中文,十年間居然有四個不同的翻譯(不是每一篇都是完整的翻譯):“錢虜懺悔錄”(天夢譯,刊《墨海》,1913年12月1期)、《慳人夢》([張]競生譯,《小說時報》,1914年1月21期),“客來及特之耶穌聖誕節”(蘇梅譯,刊《文藝會刊》,1919年3期),以及1920、1923年出版的上下兩冊的《西樓鬼語》(林紓與陳家麟合譯,商務出版)。可見當時人對這本書的熱情還更甚於後來的《雙城記》(1928年才有全譯本)。
以上談的是《聖誕頌歌》在中文世界流傳的大略。很有趣的是它的日文翻譯好像是晚到1926年才出現。至於殖民地的臺灣,因為日本政府控制外文書籍流通,所以大部分臺灣的讀書人只能依賴日文的翻譯。這些日文譯本自然流傳不廣,有能力閱讀的人非常有限。中文的出版品一樣受到管制,但是因為是同屬於「漢字文化圈」的關係,能讀懂中文的人較多,只是畢竟還是有限,所以當時英國來臺的傳教士替一般人設計的羅馬拼音「白話字」就成了一個攝取知識的方便途徑。有的知識人雖然在日本讀書,卻寧可用白話字發表他們的意見,介紹時事,翻譯西洋名著。在日本同志社大學讀書,並成為該校橄欖球隊隊長,帶領球隊贏了日本全國冠軍的陳清忠(1895-1960)就是一個例子。他回臺灣以後,捨棄日文,積極用臺語白話字寫作,並且成了臺灣第一個翻譯《聖誕頌歌》(翻譯為《聖誕歌》Sèng-tàn kua)為白話字的人(出版於1925年。時在1925年,甚至於早過日文的翻譯。
關於陳清忠的事跡,中文維基百科有簡短的記載。可惜的是這篇傳記沒有一句話提到他在寫作和翻譯上面所做的貢獻。事實上,他曾經翻譯了好幾位英國及法國詩人的作品,例如Chaucer, Arnold, Browning, Maupassant 等。後來他也曾經翻譯《威尼斯商人》(可惜手稿已經散失)。這些努力非常令人佩服。由於他的寫作充滿基督教的信仰,我們可以稱他為臺灣的C. S. Lewis。
想起小時候母親用臺語講《威尼斯商人》給我聽,初二時在臺南長榮中學看全本《聖誕頌歌》的演出,當時也是全部臺語對白,印象都很深刻。如今已是老耄之年,仍然記得許多現在年輕人已經不懂的語詞或發音,不免有許多感慨。同時,眼看著對岸的文學界,現在又再一次不能完全自由閲讀中西文學名著,當然更是感繋良多。(2021年雙十節與美東華萍澤)
李弘祺小檔案
1968年歷史系畢業,耶魯大學博士。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紐約市立大學、臺灣交通大學,也曾在本校、清華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擔任講座教授或特聘教授。專攻中國教育史、著有傳統中國教育的中英日德義文專書及文章數十種,以《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為最重要,獲中國鳳凰衛視國學成果獎及國家圖書館文津獎。日本關西大學《泊園》學刊稱許為「當今世上治中國教育及科舉第一人」。李教授也經常講授有關近代西洋思想的課題,主持台積電及敏隆講座。現與夫人退休於美國赫貞河畔的華濱澤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