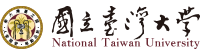臺大上任當時的回憶
昭和5年(1930)我到臺大赴任,恰逢霧社事件[註1]過後不久,來到台北總覺得自己到了一個不得了的地方,心境不太平穩。搭乘從基隆出發前往台北的火車,窗外的風景果然與日本大不相同,不知為何我只覺得非常寂寞。或許是這樣的陰影所致,我擔心泰雅族人在台北徘徊走動,若不小心謹慎些,恐怕項上人頭不保。但是,當我抵達台北後發現,這裡是個漂亮的城市,多數為日本人且與日本當地的城市相差不遠,完全看不見長得像生番一般的人,隨即鬆了一口氣,安心下來,之後,我參觀了大稻埕與萬華,果然還是覺得自己到了不同民族所居住的城市,多少有些緊張。
.jpg)
圖:大稻埕,作為臺北市的漢人街,大稻埕的永樂町市場是臺灣人買賣最興盛的地方。衣服、食品、古董與日常用品等等的買賣都在以簡易搭蓬且並列的攤位上進行,叫賣聲、拉客用的胡弓月琴聲、中國戲劇的銅鑼嗩吶吵雜聲,雜然喧囂到想要把耳朵摀住那般地興盛。出處:山本三生等編。《日本地理大系第十一卷臺灣篇》。昭和5年(1930)。(典藏者:中央研究院。發佈於《開放博物館》)
抵達台北下榻旅館當晚,我兩歲的小孩因急性腸黏膜炎發燒,隔天依照鎮上醫生的建議前往臺大附屬醫院住院。我們於新公園的入口處搭乘人力車,橫越公園百米左右直到出口處,才發覺明明醫院近在眼前,不由得微微露出苦笑。幸運的是,孩子的病在短短幾天內被治癒。我們抵達事先預訂的房子時,為我們導覽的是商人水野先生,他為我們買來了漂亮的麻質蚊帳,猶記當時我因他的行為感到些許奇怪,我說11月在日本當地是不需要使用蚊帳的,不明白為什麼這個時期還需要為我們準備這樣的東西。話說回來,到了當天晚上我才第一次知道蚊帳的必要性,在此之後的16餘年間,蚊帳是我們每日不可或缺的物品,助益良多。
到了年末,打算如同在札幌的時候一樣準備年糕而訂購了一斗左右。但我這個行為其實非常失敗,因為數日未取出,年糕上長滿綠色的黴菌,最後連一口都沒吃,全都丟掉。元旦當日食用年糕時,因為天氣太熱,我裸著身享用。哎呀!深深感覺到臺灣實在是個很熱的地方。而今年七星山降雪,台北的人們為了看雪登上七星山,聽說登山者之中也有盲人,我略為感到驚訝。剛到臺大上任就接連遇到許多令人感到驚訝的事情。
我在北海道大學擔任助教的時候,曾因微薄的薪水感到苦惱,來到臺大後,除了平時的薪俸外,另加了5成的薪水,也提供住宿費用,生活寬裕了不少。哎呀!正當覺得自己終於可以存到錢的時候,轉眼間又多了許多用錢之處,生活變得有些奢侈。在臺灣生活的16年間無法好好存錢,戰爭結束後回國之際,一人僅能攜帶規定的1萬日元,抵達國內後,面對高額的物價實在是束手無策。反正白領階級的錢包體積是一生都不會膨脹的。
.jpg)
圖:加藤浩任臺北帝國大學助教授、俸給、勤務(1930-10-01),〈昭和五年十月至十二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等官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檔案.進退原議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062017)
我是在霧社事件結束後到臺灣赴任的,記得當時自己並不安心,後來在太魯閣峽谷與泰雅族人碰面時,我再次感到不安、害怕。太魯閣峽谷今日已有漂亮的聯外道路,泰雅族的女性以舞蹈歡迎觀光客來訪,但我們當初訪問的時候,位於向上看1千呎、往下看也有1千呎的地方,路面僅容1人可以通行的狹窄道路,經由此路前往原住民所在的聚落,無論往上或往下看都令人頭昏眼花。雖然事前已獲得前往蕃社的許可,並且有持槍的警察為我們帶路,令人感到安心,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前往蕃社若沒有警察一同前往就無法安心的危險程度,心情非常複雜。
偶爾遇到年輕的泰雅族人,他們會說「你好」並點頭經過,但若是遇見年長者,直到我們通過前,他們會將身體靠在山側,以便我們先行,但不會與我們打招呼,而會以非常嚴肅的表情直直盯著我們看,再加上他們的腰間繫著番刀,實在令人不寒而慄。為我們帶路的警察曾在某地說「雖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展開以下故事:「在這裡,以前曾有間小小的派出所,1位警察單獨在這裡留守。某天早上,該名警察因為聽到有人說您好並敲擊窗戶,他將窗戶打開將頭伸出去那瞬間,一把番刀以眼睛也追不上的速度將他的頭砍落,而抱著頭的泰雅族人往1千呎下的山谷直直地垂降下去,消失了蹤影。」泰雅族人即使在地勢險峻的地方,垂直的往山谷下如降落般行進,對他們來說是很普通的事。
這天,我們在警察派出所住了一晚,隔天前往番社參觀學習,在河畔深處湧出的溫泉泡了一下湯,流流汗(挖掘大理石河床建造的溫泉池,不用說當然是露天溫泉,我們把此地稱作深見溫泉),再由警察帶路下太魯閣峽谷,返回歸家的路上。
.jpg)
圖:1938年,走在太魯閣峭壁的泰雅族人(今稱太魯閣族)(編者:Paul D. Barclay;典藏者:Lafayette Digital Repository。發佈於《開放博物館》)
.jpg)
圖:1939年攝,太魯閣立霧橋。(Michael Lewis 臺灣明信片收藏;典藏者:Lafayette Digital Repository。發佈於《開放博物館》)
戰爭結束後,大學接收團隊來到學校,團長是大正14年(1925)從北海道大學生物學科畢業的羅宗洛,我也聽聞過他的學生時代。他之所以是臺大接收團團長,是因為他向蔣介石提出建言「因為臺大的設施完善、教職人員也很優秀,希望不要解散,若能保持現狀下去,將來中國的年輕學者應該也會選擇留校」,他這麼說後,好像得到了「那就你去接收吧」的回應。當時他是上海的生物學研究所所長,他稱讚蔣介石是中國首屈一指的豪傑,是位相當有見識的大人物。
羅宗洛和接收團隊成員幾乎都是在日本接受教育,日語說得比我們還好,所幸如此在溝通、交流方面都能相互理解,「明年正式成為學校聘用教師,因為不會有待遇不好的情形發生,沒有必要現在立刻返回日本。若現在在學的學生們,到明年春天都能持受到入學以來的教育方式學習對他們比較好。與教務有關的教授會議也可以依照慣例照常舉行」(註2),誠然是胸襟寬闊的做法。因為如此,三年後學生們於昭和21年(1946)3月以出色的學士身分獲得畢業證書,從學校畢業。
.jpg)
圖:羅宗洛校長(1896-1978)
北海道帝國大學農學博士(1930)。1945年10月17日抵臺,代表國民政府負責接收臺北帝國大學。1945年11月15日與前臺北帝大總長安藤一雄完成接收手續。接收後改名「國立臺北大學」,擔任代理校長。1946年1月正式更名為「國立臺灣大學」。羅校長曾言「大學之目的在於真理之探求,為人群謀福利」。當時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傾向盡量遣返日籍人士,惟羅校長主張應先全盤接收,穩定秩序,兩人時有摩擦,後來也因此離開臺灣。
臺大的每位畢業生在許多領域都相當出色、活躍,這也令我感到開心,可惜的是,即便同學人數減少卻也沒有新加入的人,讓我感到非常寂寞。然而,臺大直至今日作為臺灣文化泉源,成長得十分出色,送走了很多畢業生,進入社會服務,身為構築如此出色大學基礎的我們亦由衷地感到喜悅,與有榮焉。舊臺大的各位及新臺大的各位,請務必成為日臺交流的橋樑,殷切期盼諸位今後在促進日臺文化的交流及國家邦交的貢獻上不停息。(原文出自《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創立六十年記念》,1988,劉盛烈教授提供)
加藤浩小檔案
1898年生(明治31年-?),日本千葉縣人。1923年(大正12年)北海道畜產農學科畢業,留校任助手。1930年(昭和5年)來臺,同年10月就任臺北帝大理農學部助教授。1935年(昭和10年)獲農學博士學位。1937年(昭和12年)起兼任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教授,負責畜產學課程及動物學特別實驗指導;1943年升任農學部畜產學・熱帶畜產學第一講座教授。期間亦兼任師範學校農業教科書調查委員會委員及臺中高等農林學校教授。
日治之初,臺灣總督府制定畜產政策,設立研究機構,引進牛畜羊馬豬等,進行飼育和品種改良,開啟臺灣近代畜產新頁。多位學有專精之畜產學專家獲聘來臺,包括在臺北帝大任教之山根甚信及加藤浩等。(參1.《臺北帝大與學術南進》,葉碧苓,2010;2.<長嶺林三郎與近代臺灣牛畜改良事業之展開>,吳文星,2014)
譯者:吳智琪/臺大圖書資訊研究所畢業
註1:霧社事件
臺灣在日治時期昭和5年(1930)發生的原住民武裝抗日事件,地點位於今南投縣仁愛鄉霧社。起因於賽德克族原住民不滿日本當局的統治,趁霧社小學校舉行運動會時,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率領族人起事。日方隨後調集大批軍警,以飛機、山炮、毒氣等武器強力鎮壓,族人不敵,最後莫那·魯道自盡,數百名族人集體自縊,生還者被強制遷到川中島(清流部落)集中看管。該事件爆發後震驚國際,造成時任總督石塚英藏等高官引咎去職。霧社事件是臺灣人在日治時期最後一次武裝行動,而且是有史以來最為慘烈的一役。魏德聖執導的電影《賽德克·巴萊》即記錄這段歷史。(圖:霧社全景,1930。文圖取自維基百科)
.jpg)
註2:羅宗洛接收後,對於用才擬定三原則:留任臺籍及日籍教師,並向國內(中國大陸)延攬。根據「行政公署及所屬各機關徵用日籍員工暫行辦法」(1945年11月頒,起自1945年11月4日,迄1947年2月21日)填寫徵用聘書,進行甄審。(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06510002001)
.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