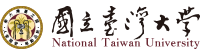溫羅汀
大約是七、八年前第一次聽到「溫羅汀」這個名詞。說真的,如果不是從唐山書店的陳隆昊老闆聽到這個名稱,我大概不會寫這篇文章。同時,我相信整天在臺大正門或新生南路出入的學生們大多也不知道它的由來。簡單地說,它是溫州街,羅斯福路和汀州街,再加上新生南路,所包圍的、而與臺大隔鄰的地方。
它是由很多的書店(包括在這裏多年的唐山、南天,以及好幾家很有模樣的新、舊書店,以及能提供咖啡的欒樹下等等),平價飲食店(最近價錢有升格的傾向),住宅雜處的地方。其實說不出來它真的有什麽風格。然而,當初臺大(特別是城鄉所)幾個有文人素養的教授們開始呼籲把這個地方發展成一個有特殊風格、能反映知識人品味的社區時,我相信最興奮、登高歡呼最多的應該是書店吧。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十多年下來,書店雖然增加了一些,卻似乎沒有讓人們覺得它像日本時代就已經開始有書店薈萃的榮町,並且逐漸發展而成為書店街的衡陽路和重慶南路一帶。這一個「文化區」到了1970年代逐漸衰落,目前看來溫羅汀還沒有能取代它。

圖1:溫羅汀有數十家書店。
.jpg)
圖2:提倡女性主義的女書店:門上掛著一張海報:明天拆政府。
溫羅汀應該是臺灣任何一個社區都比不上的有最多「博士」的地方。這樣許未必百分百正確,新竹或竹北有可能勝過溫羅汀。不過若以出入的讀書人來說,這裏應該勝過新竹的工業園區或清大及交大。這就不免使我想起波士頓沿著查爾斯河的景色;在沿河大約一哩路的旁邊,集中了最多影響世界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於人文藝術科學的各色各樣的知識人(intellectuals)。每次開車經過那裏,就讓人有一種進入希臘神廟般的敬畏感。
也許有一天,溫羅汀也會讓在那裏出入或經過的人有那樣的感覺。這不正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境界嗎?
在很多人的想像裏,溫羅汀就是臺北的神保町(一般也被稱為神田區)。集中有超過150家,號稱是世界上最大的舊書店,據說孫文和周恩來都曾經在神保町蹓躂過。對於臺灣人來說,從日本時代開始,許多人到日本留學讀書,自然也會到這個從明治中期就興起的書店街去流連買書。我父親1936到1942 年間在京都和東京讀書,所以對神田非常熟悉,我也因此從小就聽他談神田的書店。在他的藏書中讓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一套七卷本的德文狄爾泰(Dilthey)全集,據他說就是在神田的舊書店買的。數十年之後,我已經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數度到日本,當然也不免要去神保町尋寶。記得我擁有的仁井田陞的《唐律拾遺》就是在那裏買的。

圖3:世界最大的舊書街:東京的神保町。
但是坦白說,神田區雖然是買書的好地方,它卻不像是一個文人聚居,可以尋找年輕人創意和精神放肆、解脫的地方。畢竟這是日本現代高等教的起源地,所以殘留著一絲絲大學城的氣息。聽到御茶の水這個名字(與神保町的距離只是一條大街:靖國通,是書店集中的地方),那麽當然除了書店之外,大概會聞到濃郁的咖啡或咖哩的味道。但是日本有名的文人似乎更寧願選擇在遠離城市喧囂的古寺廟居住寫作。在神保町看不到幾個文學家或藝術家的紀念碑。

圖4:京都市郊的哲学の道。
在京都大學附近有一條聞名的「哲学の道」。很多人來京都都會想到這裏散步、靜默思索人生及宇宙的大問題。這條道路正式命名是1972年的事。讀過金耀基的《海德堡語絲》的人就知道這條「哲学の道」其實是仿自德國海德堡的「哲學家小徑」(Philosophenweg)。海德堡的小徑可說是19世紀初浪漫時代的產物,也是耶拿大學、杜賓根大學、多倫多大學 (Toronto,大約1901)、舊金山(2013)等同樣的小徑的原型。

圖5:海德堡的哲學家小徑。圖取自維基百科。
浪漫時代的人生理想其實是嚴肅的,他們追求的是玄思的理想。他們對浩瀚的宇宙著迷,要參透人生的目的及意義。這個是19世紀浪漫時代哲學家共同的心願,但即使到今天,一切激情已過,很多人還是希望在哲學家的小徑漫步。
不可否認的是讀書人的哲學夢畢竟需要一定的社會基礎,第一個使用「文人的理想國」(Republic of letters;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1684)這個名詞的白義耳(Pierre Bayle)所談的是由科學院院士,高貴仕女,在雜誌寫文章的有閒知識人所認同的概念。大概沒有人會否認啓蒙思想是這些人創造出來的。階級的背景會決定知識發展的方向,但是有趣的是這些活動似乎與當時的大學沒有什麽關係!
正當啓蒙思想家們在科學學院、沙龍、音樂廳或私家實驗室創造他們的共和國時,大學因為傳統的保守性格,堅持繼續使用拉丁文來作為學術的語言,因此大學生們被迫集中到巴黎大學所在的拉丁區,於是相對便宜的左岸(或許應該翻譯為河陰;因為是在塞納河的南岸,法文以相對應的左邊"Rive Gauche"稱之)文化就明顯沒落,而被新思想衝擊,從而變成了一個宣傳「對位文化」(counter-culture)的中心。19世紀中期以後,這個地方發展出以咖啡、簡餐、廉價租屋有名,住了許多嚮往波西米亞(Bohemian)生活方式和喜歡批判傳統思想的人們。大學精神和左岸變成了同義語。

圖6:文人的共和國。
最早到西方留學的中國學生就是在這個年代到了巴黎。他們看到的是混揉理性和感性的浪漫世界,是吟詠「茶花女的飲酒歌」、不斷在街頭「鬧革命」、追求玄虛的自由的天堂。難怪徐志摩說:「法蘭西淫風之甚,人口减少,安知不影響於此乎!」。
但是,中國留學生對左岸的波西米亞生活卻是羨慕的。1928年六月29日上海的《申報》刊登了這個報導:
上海的新拉丁區:在上海的西南有一所窮浪的學校居然已開辦半年了。…說起這個學校的產本來只是幾個窮藝術者集合來想做他們的「在野的藝術運動」,同時因為有一羣「有知無產」的青年想找個讀書的所在,於是他們便不顧一切努力幹了起來。各人當了許多家具,籌得了開辦費,也不求政府幫助,也不請資本家解囊。他們無錢無勢,他們的衣袋中甚麽都没有…。反過來說,他們有的只是勇氣。…至於藝院的教師像田漢、歐陽予倩、洪深、朱維基、徐志摩、徐悲鴻、陳子展、葉鼎洛諸文藝界的好漢。…這半年來因為窮學生太多,經費積欠太巨,所以開支不靈,以致無情的房東和無理的廚夫常常追著討錢,那要債之聲差不多在南國的人們已是慣聞。然而他們不顧一切,繼續在他們畫室裡、劇場中、書桌上努力工作。飢餓不算個事,離了藝術,那他們便將失了靈魂一般地要設法再生起來。
或許有一天,溫羅汀也會變成人們認同臺灣大學的一個專屬地名。(2024年四月11日於臺北旅次)
李弘祺小檔案
1968年歷史系畢業,耶魯大學博士。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紐約市立大學、臺灣交通大學,也曾在本校、清華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擔任講座教授或特聘教授。專攻中國教育史,著有傳統中國教育的中英日德義文專書及文章數十種,以《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最為重要,獲中國鳳凰衛視國學成果獎及國家圖書館文津獎。日本關西大學《泊園》學刊稱許為「當今世上治中國教育及科舉第一人」。李教授也經常講授有關近代西洋思想的課題,主持台積電及敏隆講座。現與夫人退休於美國赫貞河畔的華濱澤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