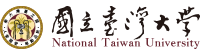研究發展


~動物倫理研究> 牠/們的故事:動物倫理研究的回望與想望
雖然長年關心動物,且近年研究方向以動物研究為主軸,但是我一開始並未試圖把個人對動物保護運動的投入延伸到學術面向上。碩士班時期我對性別研究、後殖民以及批判理論感興趣,後來以弱勢族裔研究為碩論主題。博士班時期接觸精神分析,覺得它似乎可以回應我在成長過程中對於性別身分的思考,也能幫助我釐清許多情緒產生的緣由,博論試著結合精神分析與喬伊斯研究,取得學位在系上任教後,在大學部與研究所繼續開設和精神分析相關的理論課程。真正轉向動物研究大約是2006年,那時動物研究還不像近年一般,因為後人類、新物質主義等論述的崛起而連帶受到注意。我剛開始投入這個領域時,雖然國外相關研究已有一段時間的累積,但國內尚未起步。

越來越多家庭選擇與同伴動物成為親族。(圖取自freepik,https://pse.is/5kmzqw)
回想起來,自己會有這樣的轉向,背後的關鍵因素是我的貓Kiki,牠2022年6月時以20歲的高齡過世了。我1999年就在臺大教書,可是過了七年才開設通識課「文學、動物與社會」,以我對動物議題的關心來說,算是拖蠻久的。那一年開課,是因為發現Kiki長了惡性乳腺腫瘤。那時教課與研究還沒有以動物議題為重心,不過參與臺灣的動保運動已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包括催生動保法。在Kiki生病而我什麼也不想做的那段時間,經過一番「我對動物的關心是否只侷限在自家動物上?」的自我質疑,我決定開一門與動物有關的課,透過適合的文學文本,討論如同伴動物、實驗動物、展演動物等議題,希望在用心照顧Kiki之外,也積極以教學推動動物倫理觀念,為更多動物做點什麼。後來Kiki順利康復,但我既已克服最初開課的障礙(以動物議題為授課主題,得不斷面對不忍見的動物苦難),就持續每年固定開課至今,《中國時報》與《天下雜誌》,都曾因這門動物相關的課程開設在文學院而前來採訪報導。
如前所述,國外的動物研究已累積相當的成果,對我也有頗深遠的影響。以情感在動物研究中的重要性為例,哲學家迪波黑(Vinciane Despret)與澳大利亞哲學家范道倫(Thom van Dooren)都把這個問題談得既複雜又細膩,例如凸顯「情感」(affect)這個字與「被影響」(be affected)之間的連動,以及情感如何作為行動的契機等等。另一方面,我也很認同近年不少學者主張的「回應的倫理」:責任(responsibility)這個字本身,包含回應(response)和能力(ability),能夠回應,就是負責任的一種方式。但願不願意負責任、在不同的情境下願意怎麼去回應,都可以是極其個人的,所以很難訂出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因此回應的倫理不拘泥於原則的建立,而強調回應的意願,就像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所指出的,如果真的有一套可以一體適用所有狀況的倫理準則,那僅是照表操課,像機器的自動反應一般。這種可以「預先做好」的倫理決定基本上是自我解構的,稱不上涉及正義或責任(Rogues84-85),畢竟倫理牽涉的是面對某一個特殊的生命對我們做出召喚時,我們當下決定如何回應——你願意為這個生命負怎樣的責任?由於我非常在意理論的實踐性,回應的倫理可以說是最能因應不同狀況去推動動保運動的一套說法,我也就特別有認同感。需要強調的是,「回應的意願」看似發自感性,不等於不客觀、不科學或缺乏價值判斷:錢永祥《人性之鏡:動物倫理的歷史與哲學》第13講〈德性倫理:從情感回到自身〉提到,情緒和認知、解讀、判斷都有關,我們一直把情緒當成是負面的,他反而覺得「情緒才是行為的實際推動力。『知』不一定帶來『行』;『知』牽動了情緒,才會轉成行動」(182)。錢老師對德性倫理的強調,和之前我援引的情感相關理論,同樣都能稍稍平衡目前的主流論述過度貶抑感性的現況,也有助於推展理論的實踐性。
早在102年申請國科會專題計畫時,我已開始關注回應的倫理。當時所提的三年期計畫主題是「對他者的(無)回應:重探自戀」,那時候注意到當代的自戀轉向──例如健身美容的蔚為時尚,讓我好奇當人們把很多的精力放在所謂的「自我養成」時,我們還會有餘裕關心他者嗎?乍看之下,不論是對身體或身體形象的過度投注,還是愛自己遠勝過愛他者的「自戀」,確實可能妨礙倫理議題的思考。我當時關心的,是自戀與倫理行為之間的牽連互動是否並非單純的「一消一長」,以及從自戀中是否有可能發展出一種回到自身、關注自身而後再朝向他者開放的力量?
回到自身與向他者開放是否互斥?在檢視人與同伴動物的關係時,我們或許也可以再次思考這個問題。我覺得人只要發現自己關心在意同伴動物的程度更勝家人朋友,幾乎都會自我譴責或感到不安,因為我們受到人類親屬關係的羈絆還是很深,而且多半已經內化了「不應該對動物比對人還好」的想法。但換個方式來想,其實會不會我們和非人他者所建立的親族關係,可以讓我們回過頭來檢視與人類家人之間的關係,從而思考「成為親族」(making kin)的對象或許不僅限於自己家人或和自身相同的物種,而能與他者之間也建立不具壓迫性的、跳脫人類中心主義式的連結羈絆?我所謂回過頭來思考人與人的親族關係,指的是當你跟動物很親、願意為動物付出很多時,確實可能開始自問:我對動物都可以做到這個程度,對人為什麼不可以?是因為我對親人的要求太嚴苛、期待不同?還是有其他因素?對人這個與我同類的物種,我能做出一些配合和調整嗎?也就是說,很理想性地,和動物的關係有可能可以訓練我們去做到法國學者伊希嘉黑(Luce Irigaray)所說的 “I love to you” (J’aime á toi) 的狀態,也就是保持距離的一種愛的方式。伊希嘉黑用J’aime á toi來替代Je t’aime,是想透過á一字的介入,強調愛不應該是作為主詞的我,以一種直接掌控的方式來對待對方,對方和我之間是有距離的,他是不可化約的、具有回饋可能性的,並不只是個被我愛的對象而已。在越來越多家庭選擇與同伴動物成為親族的今天,我希望上述這種人文視角的切入,能有助於思考某些現象的崛起可能帶來的變化。
目前我正進行的國科會計畫「與多物種共哀:動物研究的未來」,某種程度上延續我想要結合精神分析和動物研究的企圖,只是在思考如何回應動物的問題時,更聚焦在「哀悼」這種情緒。我發現哈洛威(Donna Haraway)與范道倫等學者倡議的「與動物共哀」,或與之近似且相關的概念,如哀悼的倫理、為死者代言等等,還有許多可以深入探討的面向,因此希望透過「共哀」這個關鍵詞,對人與動物關係進行的新思考。就具體成果而言,我和黃宗潔合編的《動物關鍵字:30把鑰匙打開散文中的牠者世界》已經完稿,在這本包含散文與評析兩部分的選集中,我們以一個關鍵字搭配一篇所收錄的散文,從關懷動物的角度切入,撰寫我們對該篇散文的回應,希望結合文學與評析的面向,把原屬學院範疇的動物研究,帶向更多讀者,期待我們能為動物做的,不總只是傷逝與哀悼,也期望動物研究的未來,有更好的可能發生。(本專題策畫/臺灣文學研究所黃美娥教授&法律學系陳韻如教授)
註:本文初稿由侯淇齡整理自〈與動物共哀:非人研究的情感轉向〉(王榆晴訪談紀錄,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電子報第43期),作者黃宗慧本人編修,陳文琳校對。
參考書目:
[1]錢永祥。〈德性倫理:從情感回到自身〉。《人性之鏡:動物倫理的歷史與哲學》。臺北:聯經,2023,頁179-192。
[2]Derrida, Jacques. “The Future of the Profession or the University without Condition (Thanks to the ‘Humanities,’ What Could Take Place Tomorrow).”Jacques Derrida and the Humanities: A Critical Reader, edited by Tom Cohen, Cambridge UP, 2002, pp. 24-57.
[3]---. Rogues: Two Essays on Reason. Trans. Pascale-Anne Brault and Michael Naas. Stanford: Stanford UP, 2005.
[4]Haraway, Donna.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Duke UP, 2016.
[5]Irigaray, Luce. “I Love to You.” I Love to You: Sketch for a Felicity within History. Translated by Alison Martin, Routledge,1996,pp.109-113.
黃宗慧小檔案
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常自嘲以動保為主業,教書為副業。學術研究專長為精神分析與動物研究,個人研究興趣為家中貓與龜的日常生活點滴。曾任《中外文學》總編輯、NTU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主編。著有《以動物為鏡:12堂人與動物關係的生命思辨課》,編有《臺灣動物小說選》,合編有《放牠的手在你心上》、《動物關鍵字:30把鑰匙打開散文中的牠者世界》(與黃宗潔合編,即將出版)。與黃宗潔合著之《就算牠沒有臉:在人類世思考動物倫理與生命教育的12道難題》曾入圍2022臺灣文學金典獎,並獲書評媒體Openbook 2021好書獎(年度生活書類)。
2018年獲臺大106學年度教學傑出獎;研究計畫「從精神分析之鏡/外看動物他者」(2007-2010) 曾獲國科會遴選為優秀年輕學者計畫。現為國科會外文學門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