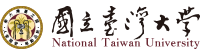"如果"成就了我的人生
我的人生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So many ”if” in my life. 看似缺乏奮鬥目標,不盡符合社會的價值觀,卻也因此不設限,能把握機會,走出和當時代同儕不一樣的人生。
考臺大是此生唯一的確定
我出生在日本,1946年跟著家人回來臺灣,當時連臺語都不會講更遑論國語,在成功中學念六年書,準備考大學。我人生中只有這一件事是自己設定目標並且完成的,那就是考上臺大。
1953年是第一屆聯招,名為大學聯招,其實真正的大學只有臺大。我報考第一類組,先填志願(可同時填第二類組),結果考進商學系。大一時共同科目多,在校本部上課,教室在學校大門入口左側平房,二年級起到法學院上課。法學院有四個系,不論系別,畢業證書都是法學士,很特別。
大三轉經濟系,和黃演鈔、羅福全成為同學。之所以轉系,原因是"商學"聽起來比較像生意人,我不是很有興趣,父親也認為經濟系涉獵的範圍較廣。臺大四年對我後來工作很有幫助,因為有商學和經濟兩系的同學,人脈加倍多,再加上成功中學的同學也有相當比例就讀法學院。
相較於商學系少有博士級老師,當時經濟系有多位東大畢業的臺籍教授如戴炎輝、張漢裕和蔡章霖,他們的學問都很好,但必須用不熟悉的國語講課,學生聽不大懂,所以老師有時會寫講義發給學生。也不只有臺灣人國語不好,從中國大陸來的老師有口音,如教高等會計的朱國章老師是上海人,他講的國語我們都聽不懂。所以我的學習大部分input是用眼睛看,考大學看的是日文版的四書五經、英文。對母語不熟悉對國語又很陌生,只能以閱讀為主。
進入經濟系才發現,老師以講授經濟史居多,歷史不會變,課本上都有,對我缺少吸引力,慢慢地去上課的時間越來越少,要考試時向學長借本筆記,照樣考得好。現在經濟系課程不一樣,大部分是數理經濟。經濟學理論不能應用在現代社會就是過時。
我想在老師眼中,我不是喜歡念書的學生,跟老師互動很少。我印象比較深刻的老師是系主任張漢裕,上課時在桌上放一個威士忌小瓶子,講課當中會開來喝,我們都在猜瓶子裡裝的是什麼,是藥是茶還是酒?這疑問永遠無解。
沒有社團活動的校園生活
課堂之外,休閒時間跟成功中學男同學一起打網球、去新店或烏來釣溪哥。那是個男女授受不親的年代,跟女同學幾乎不往來,如要交往就是以結婚為前提,不敢隨便,不過大四時認識了一位外文系女同學。沒有社團,只有代聯會辦的活動,我大一當副班代,那年錢復當選主席(一般是要國民黨黨員才會當選),大二時有個高一屆政治系學長(後來去當日本大使)拱一位女僑生出來競選,實際由他掌握會務,他擔任總務組長,找我做副組長,曾經去鳳山勞軍,也是有趣的經驗。
那時在戒嚴時期(1949年5月19日頒佈,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令),連跳舞都被禁止,只有一個地方例外即國際學舍,幾個月就會辦舞會。要參加必須攜女伴,我大三時還沒女朋友,曾拜託表妹陪我去。我們畢業的謝師宴在法學院禮堂辦桌,吃完飯後竟然有舞會,可想而知後果是什麼,學校記班代兩個大過,他不會跳舞,真是為他叫屈。
3篇論文用3種語言寫成
1958年畢業後服兵役,我是預備軍官第七期,商學系和經濟系至少三分之一的同學被分發到空軍。那時設備不足,我們沒配到鋼盔、綁腿,一小隊20人只有18支步槍,排頭排尾都沒配槍,我180公分高,排頭小隊長,只打過幾發子彈,不用擦槍,樂得輕鬆。在東港三個月後,被調來台北,再轉到空軍總部人事室,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當官,職銜是「統計業務官」,總計當兵一年七個月。1960年3月18日退伍,隨即準備出國。
對經濟系和商學系畢業生來說,最好的工作或說鐵飯碗是進入銀行、海關,我大部分同學都在金融業服務,如果我沒出國,應該也一樣,但出國並非我的選擇,甚至可以說是被「逼」來的。我念了三個大學,分別在三個國家,用三種語言寫論文。父親謝國城就讀早稻田大學,在他畢業那年我出生。他回臺灣後,創辦了早稻田臺灣校友會並兼任會長。我當兵期間校長來訪,他說你小孩都沒來念母校,父親說大兒子服完兵役就去。我是這樣去早稻田大學讀研究所的,不過我蠻喜歡在日本的生活。後來發生了一件事,導致我畢業後轉赴美國讀書工作十多年。1962年我被拱出來參選留日中國學生會長,當時會長都是由大使館推派國民黨員擔任,拱我的後來都成了臺獨分子,但我不是國民黨員,更不是臺獨分子。選舉很激烈,結果我們勝選,這讓我們壯膽。第一次開幹部會議時,大使館文化參事不請自來列席指導,我把他趕了出去。事後才驚覺"慘了",不敢回來,又不能待在日本(那時代日本公司不聘外國人),畢業後要去哪?那就去美國?先在紐約讀語言學校再申請大學,只要學校給我獎學金我就念。那時臺灣的國民所得一年400元美金,美金和台幣1比40(我當兵前曾短期在彰銀工作,一個月薪水900元新台幣),父親不可能提供我高額學費,所以我只跟父親拿500美金買機票,後來他又給我1800美金當生活費,但單單保證金就要2400元,所以我向比我先到美國的表姐夫借錢湊齊款項。
就這樣我來到紐約。UCLA和Berkley都答應給我獎學金,而UCLA加碼免學費,所以我就坐了五天五夜的大巴從紐約到洛杉磯(80元美金,比飛機省一半的錢)。我有日本碩士學位,可以當助教,月薪320元。當時流行一句話「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幾乎去美國讀書的人都不想回來,不全然是政治因素,而是兩地生活水平差很大。取得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企管博士學位後開始找工作,雖然南加大給我教職,我還是傾向去業界。本來已決定到東部一家上市公司任職,就在準備搬家之際,系主任打電話來遊說,考慮到家人喜歡洛杉磯的生活,就留下來教書,一教7年,連同在學時兼課,我的教學生涯10年。
搶救致新半導體造就巔峰
教書滿7年,有半年休假,回臺灣過聖誕節,已是我離鄉17年後。有一天,許遠東來訪,他是臺大學長,像是我大哥。他說政府在籌備三家票券公司,這也許是一個回臺工作的機會。我回美國後寫信給父親表示有意願,後來就被安排進國票任副總。1976年我回來時,歸國學人很少,學企管的更少,所以也受邀分別在美軍顧問團臺灣南加大分校和東吳大學電子計算機應用科學系教書(兼系主任),同時兼任三份工作,很忙碌。
旅外多年回國,我終於進入金融業服務,圓了父親的願望。沒想後來又有大轉折。父親和日本先鋒(PIONEER)公司的石塚社長熟識,他來臺灣勘查市場,和父親餐敘時我作陪,他表示臺灣代理商多年做得不理想,忽然轉向我問「你來做如何?」我微笑沒回答,他以為我同意,回日本就在公司董事會上宣布。隨即他們的國際部長來臺灣,雖得知詳情,還是說我必須接,我就請託在大同公司的同學當總經理,我父親任董事長,1978年百韻公司成立。兩年半後我辭去國票職務,全心經營,後來與日本先鋒合資,成為臺灣先鋒公司,打造臺灣音響界第一。
至於1999年進入致新科技公司也是偶然。致新是致福的子公司,致福被光寶合併,擬將賠錢的子公司結束,吳錦川博士為了讓公司能繼續經營,四處尋求資金而找到我。我欣賞他的無私,應允投資,擔任董事長前二年未領薪水,所幸不久即轉虧為盈,榮景看好。運氣好是原因之一,我進致新公司的第一個工作就是讓員工入股,齊心合力打拼。公司是大家的,要一起努力,我從沒安插自己家族的人進公司,現在公司紅利高,福利好,年年調薪。
大學第一志願是電機系,未能如願,現在竟要接手管理半導體公司。我跟吳總經理說,我不懂IC設計,你是臺大電機系,是專家,研發和一般管理完全交給你,財務就由我來負責。我今年87歲,是國內現任高科技公司董事長當中最年長的,張忠謀86歲退休,我預定明年6月退休。
"如果"造就精彩的職涯
這就是我的職業生涯,換來換去換了不少工作。我的個性崇尚自由,無法忍受在一個單位待到65歲退休。我回國時,臺灣經濟尚未起飛,在國票的月薪25000元,和在美國教職有段落差,很多朋友覺得奇怪我為什麼回來,然而即使不回來,以我的個性也會辭職。我不是學者型的人,尤其讀的是統計,統計不是學問,是工具,在統計領域做研究難有創新,對我來說,這樣的教書生活難有熱情持續。這和一般人以安定為先的想法背道而馳。現在年輕人念書就不太考慮到這點,愛讀什麼就讀什麼,我的兩個女兒念MBA,後來也沒在工作。讀書和工作不一定要連結,和興趣相符最重要。
我的人生充滿"如果"。如果沒去日本,不知會怎樣?如果沒去美國讀書,不知會怎樣?如果沒去教書,不知會怎樣?如果沒回臺灣,不知會怎樣?我是當時臺灣金融界最年輕的副總,如果在國票待下去一定會成為總經理,當時政府也找過我問我有沒有意願替國家做事,就是要當官的意思,但我不想。現在回頭看,就這件事,沒有"如果"。
行有餘力,去年寄付(捐款)給母校表達我的感恩,捐款分三部分,一是總圖書館修繕費4800萬,二是給經濟系新進教師獎助金暨博士生獎學金永續基金2700萬,三是給國際學院國際學生獎助學金永續基金2625萬。錢要用才有用,放在銀行最沒用,實業家邱永漢曾說:「錢賺來是半成品,用了才是完成品。」美國很多學校都以人名命名紀念捐款者,臺灣捐款給大學的風氣不如美國興盛,我認為臺大為國家培育非常優秀的人才,出自臺大,當盡己力,回饋母校、回饋社會。
謝南強小檔案
學歷:
1954-58臺灣大學商學系、經濟系
1960-62早稻田大學大學院商學研究所
1964-70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企管博士(統計學專修)
經歷:
1970-76美國南加州大學教授
1976國際票券公司副總經理兼財務經理
1978創立百韻公司
1989先鋒公司董事長
1999-致新科技董事長
服務:
工商協進會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理事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理事、副理事長
謝國城棒球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臺日交流協會理事
東海大學董事會董事
東亞經濟會議委員、副幹事長